文学论文哪里有?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经典要分为“恒态经典”(static canon)与“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顾名思义,前者指代的是那些经历大浪淘沙几百甚至上千年而不朽的经典,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鲜明的时代风格,具备艺术与人生双重的象征性、超越性与普世价值。而“动态经典”是一种相对的、历时性的经典形态。两者之间的分野在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差异性。此处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稍有不同。
第一章 《活着》经典化的建构之路
第一节 初出茅庐:小说的问世
1992 年,余华完成了自己的新作品,这部被命名为《活着》的七万字中篇小说发表在《收获》1992 年第 6 期。《收获》是中国文学重镇之一、文学风向的旗头,从这里走出的知名作家无数。以纯文学相标榜的《收获》自 1957 年创刊以来几遭起落,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余华与《收获》的缘分亦是不浅。如果说余华的文学之旅起航于《北京文学》,那么《收获》无疑将作家带入了文学史中,我们会看到这份期刊将在余华的整个生涯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从 1987 年第 5 期的《四月三日事件》开始,余华在《收获》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先锋小说(1987 年第 6 期的《一九八六年》、1988 年第 5 期《世事如烟》、1988 年第 6 期《难逃劫数》),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先锋作家的文坛地位。余华与《收获》的姻缘还体现在,90 年代他的三部重要长篇小说都发表在《收获》上。作家本人曾不无深情地表陈心迹,谈到《收获》在自己写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我有超过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在这本杂志上的。两种原因,一种是浪漫主义原因,《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小说,别的杂志根本就不可能发表,在那个时代,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发表。《收获》杂志不仅能发表我的作品,而且是完整发表”[1]。在政治审查制度仍旧严苛的年代,《收获》以其大度与包容,为一代作家的成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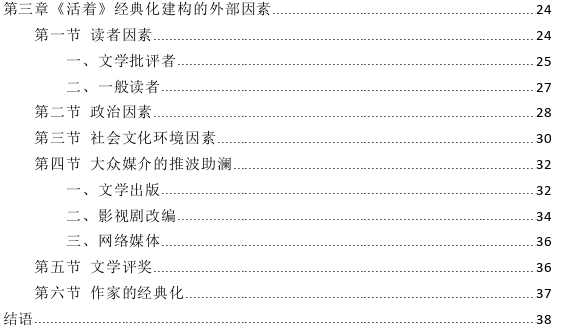
第二章 《活着》经典化的内部因素
第一节 《活着》的思想性
余华曾对这部得意之作做过许多次的阐释,最著名的莫过于 1993 年小说出版时自序中的“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作为作者的原意阐释,这段话对于小说的理解是如此意义非凡,它饱含辩证思维,成为小说思想性的最好注解。
福贵活着的一生是不断受难的一生,他的人生就像不断下降的抛物线,没有否极泰来,也没有峰回路转,只有无尽的坠落。这般密集的苦难如此扎眼,福贵很难在苦痛之间的缝隙中觅得反抗的良机、采取有效的方式,以至于一生都逆来顺受。这样的生命是看起来令人气馁,也令人气愤、怒其不争,难怪会有评论以此为矛,对《活着》大加挞伐,认为余华尊“福贵为偶像”,期盼自己乃至中国人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福贵似乎一跃成为了“乡土中国文化的智者与仁者”,他信守的是儒道的信念,“冷酷剥夺弱势群体的孤苦诉告权的同时,又慷慨地豁免了现世秩序及其历史本应承担的道义与政治责任。”[2]王达敏也认为“《活着》是写给那些如今年龄在 45 岁以上,并且家庭或个人曾不同程度地遭受过如同福贵一样苦难的人看的。”[3]这些人人到中年,体验过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苦大难,深切了解了生活的艰难和活着的不易,便更能与《活着》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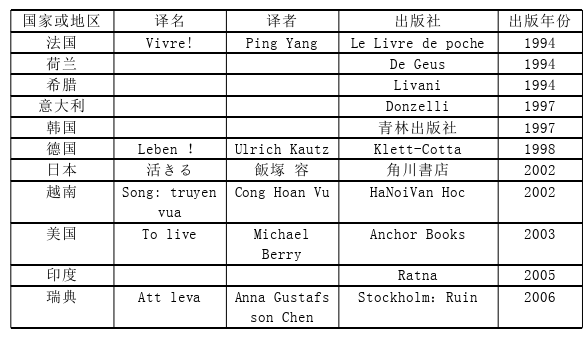
第三章《活着》经典化建构的外部因素
第一节 读者因素
艾布拉姆斯曾在其著作《镜与灯》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在他的理论构想之中,读者作为文学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学场域中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成分,而是具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力。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内容与表达都随着读者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在此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的历史也不为过。在后世出土的西周古墓中,人们发现了老子的《道德经》,据此可见,在那个时代,《道德经》便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为贵族所认同,这成为《道德经》能够流传后世的重要原因。虽然在古代并没有理论的指导,但是人们的行为却充分地说明了读者对于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意义。而在当代,读者在作品经典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越发重要。离开了读者的阅读与再创造,文学的经典化便无从谈起。经典不会自动地呈现,一定要在读者的阅读、阐释、评价过程中才会呈现其价值。“一个作家和作品得到了权威的赏识和推荐之后,能不能真正成为文学经典,还有待广大读者和批评者的主动阅读和欣赏。”
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有两类读者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类是文学批评者,另一类是普通的读者。文学批评家凭借着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专业化解读,将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剖析,并将这种分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普罗大众,从而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广大的普通读者则通过文学阅读等形式参与到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建构中来。
第二节 政治因素
经典化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学者评论、教科书和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定位以及读者阅读之外,社会环境、媒介传播、影视剧改编等都影响着经典化的进程。首先,政治文化语境对于《活着》的影响是探讨其在多重社会历史环境中存在境遇的关键因素,政治权力从多个方面影响着作品的传播,因此作用于作品的经典化。因为经典“背后无疑隐藏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 [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不仅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钳制思想与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1]建构经典事关话语权力的分配,那么统治者通过政治权力推行自己的经典就显得无可厚非。在政治对文学作品生命的作用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书报审查制度——它是文艺作品能否顺利进行文学生产的“拦路虎”。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文艺作品因为政治敏感因素而无法顺利出版,或者在出版后旋即被封禁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纳入国家机制之中,由党直接进行一元化管理。作家的创作必须在国家意识形态设置的框架内进行,其主要功能是对国家政策进行文艺化的阐释。传媒的运作与各种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以其强大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为文学生产机制的更新推波助澜。一方面推出契合时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借助一次次的批判和论争来干预、淘汰和矫正文学创作的倾向”[2]。所幸小说《活着》并没有遭遇这种刁难。虽然涉及到文革和建国后的几次运动,但是小说对这些场景的处理“避重就轻”,强调了克制隐忍的一面,而不是不幸、悲惨和抗争的一面。这种处理更容易得到权力的认同,因此能在权力话语的审查之下获得其“合法地位”。
结语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文学艺术,亦复如斯。问世近三十年来,《活着》失落过:批评界“众声哑然”,出版千册,销路不畅;《活着》轰动过:获意国文学奖,销量持续走高;《活着》不幸过:时代变革,纯文学式微;《活着》也幸运过:因电影改编而声名远播,因打动人心而家喻户晓;《活着》更是受到争议,且这争议将会继续下去。在众声喧哗之中,学术界、出版机构、教育体系、批评家、读者尽数参与其中,共同造就丰富多彩的接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活着》从同时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成为这个时代传给后世的文学记忆,这种记忆的传承贯穿人类整个文明史,让后人知晓这个时代曾在文学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杰出成就,我想,这便是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经典要分为“恒态经典”(static canon)与“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顾名思义,前者指代的是那些经历大浪淘沙几百甚至上千年而不朽的经典,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鲜明的时代风格,具备艺术与人生双重的象征性、超越性与普世价值。而“动态经典”是一种相对的、历时性的经典形态。两者之间的分野在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差异性。此处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稍有不同。托托西认为,审美价值更偏向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愉悦。这种愉悦感越强烈,对其产生兴趣的读者越多,审美价值则越高。但是,这种审美价值是不稳定的,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兴奋总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难以预测的改变,因此,有的作品甫一出版便迅速走俏,不久却无人问津;有的作品发表时备受冷落,稍后却如鲜花重放,正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一般而言,文学的审美价值正如同壁画色彩会随时间而消褪,新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审美对象日渐多元与丰富,欣赏者也是代代更替,人们不可能永远享用同一个审美对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丧失了审美主体的文学作品将会迅速黯淡。而有些作品在审美价值之外,还存在着出众的艺术价值,或为对家国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刻思索,或为对人生经验深入浅出的明快诉说,或为对人性善恶洞如观火的犀利评判。这些才是支撑一部作品流传千古的重要秘密,这不同于会因为审美取向的变迁而轻易改变的审美价值而具有更加恒久的艺术魅力,从而吸引一代代读者的目光,不断在时间长河的淘洗中增值。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