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周作人和邵洵美等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即便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但是在初接触唯美主义思潮时,他们也并非一张白纸,文学传统、文化心理、个人气质、社会历史背景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异国思想的接受,思想的传播与商品贸易不同,无法在传播中保持原貌,他们对唯美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表达带有个人化或本民族化特点是完全合理的。
第一章 晚清文学中的“唯美”迹象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中的末世隐忧
基于对个人前途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双重担忧,晚清小说中不乏表现悲观失望情绪的文字,其中的代表作品是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吴趼人(1866-1910 )的《上海游骖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1872—1935)的《孽海花》等作品。
刘鹗 1903 年发表的小说《老残游记》是一部充满着颓丧绝望情感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叫“铁英”,号“补残”,“补残”这个名字来自于他对“懒残和尚煨芋”这一故事的仰慕。在这个故事里,一位前途无望的书生因为获得了高僧的指点而当上了宰相,这种幸事想必也是“铁英”,或者说是刘鹗本人的梦想。但即使自名“补残”,成为一国宰相的梦想却随着清朝的衰落成为了一件毫无希望的事。“补残”的希望破灭后,便成了行走江湖的郎中“老残”,从读书人变成了江湖郎中,从救国变成了救人,从踌躇满志变得穷困潦倒起来。
小说开头的沉船情节常常被理解为清王朝末世的隐喻,在小说第一回,“老残”与友人原本计划看日出,却看到海上漂泊的一艘岌岌可危的大船,大船即将倾塌,船上的人却推卸责任、自相残杀。“老残”拿着一个“最准的向盘”打算营救船上的人,却被对方狠狠打击,情急之下,才发现这是一场梦而已。在这个片段里,民族和个人都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这正如小说第一回的标题“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更可悲的是,手拿药方或者方向盘的文人得不到重用,他们的个人前途遭到打击,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民族的危难。这个带有预言性质的“沉船之梦”既是小说的开头,也是一个旧世界的结局。面对这种似乎无力回天的结局,作者也只能慨叹:“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如果说《老残游记》表达了对旧世界的绝望,那么吴趼人的小说《上海游骖录》表现的就是对初露锋芒的新世界的失望。《上海游骖录》发表于 1907 年,讲述的是年轻的书生“辜望延”为躲避灾祸去上海避难的经历,来到上海的年轻人本希望向“革命党”求救,却发现所谓的“革命党”在上海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有的沉迷于鸦片,有的浪迹于青楼,与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小说还借“李若愚”之口宣扬“厌世主义”和“醇酒妇人主义”。除了《上海游骖录》以外,吴趼人还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借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来表现社会的末日图景,官场与商场都是肮脏不堪之地,人伦纲常和道德秩序也被破坏得体无完肤,整个社会都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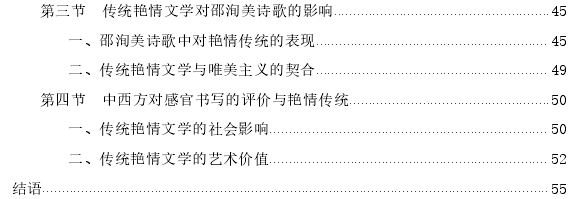
第二章 “美文”的唯美风格与晚明余韵
第一节 “美文”的含义与主要特征
一、“美文”概念的用法
提起“美文”,许多人会想起周作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创作了大量雅俗共赏的“美文”,还因为他在 1921 年 6 月 8 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文》的短文,比较明确地对“美文”的含义进行了解释: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出,周作人比较强调“美文”概念的外国“基因”,认为“美文”是一种艺术性较强的外国论文,强调它纯文学的一面。在提出这一概念的同时,周作人也开始进行“美文”的创作,他写于同年的系列散文《夏夜梦》后来就得到了同样推崇美文的诗人朱湘的赞美,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叫做《统一局》的短故事,被诗人朱湘认为是“一朵微妙的散文‘蔷薇’。”
“美文”虽然与周作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个概念却并不是他的发明。我们在这里简要列举王国维、谢无量、梁启超关于“美文”概念的使用情况,以便大致了解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的语境。
1907 年王国维发表《倍根小传》,详细介绍了英国散文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生平与文学成就,这篇文章“是我国最早比较详细介绍英国这位科学哲学与散文大家的文字材料。”45在文章的最后,王国维指出:“倍根之文,可代表当时秾丽散文之极致,虽以彼之冷静圆熟,犹不免有几分美文之病,是可见当时诗的时世影响之大矣。”
第三章 感官书写的唯美倾向与艳情传统
第一节 邵洵美诗歌中的感官书写
当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文人沉浸在清雅的“性灵”世界时,对人的肉体的注视和描绘在上海这座城市得到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张扬。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邵洵美,他的代表作《花一般的罪恶》被解志熙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歌颂感官快乐主义的诗作。”
一、邵洵美感官书写的两种类型
对人体的关注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强调对感官的描绘,这些描绘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写诗人主观的视听感觉,通过描写声音、色彩等外部刺激来表现创作主体的感官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二是将人体客观化,直接描绘肉体的形态,从而给读者一种想象上的刺激。这两种书写类型有时会发生重合,比如诗歌的创作主体常常是男性视角,因而也多以抒发男性的主观体验为主,而当诗歌中出现对女性肉体的直接描绘时,这种描绘也成为了视听刺激的一种。
这些感官描绘当然并不仅限于海派作家,只是在上海这座现代都市文化的酝酿中,感官书写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表达。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以文学社团或期刊划分不同的作家群体,就感官书写而言,涉及到的作家主要有以邵洵美、滕固、章克标为代表的狮吼社,以及在《金屋月刊》上发表作品的相关作家;以曾朴、曾虚白为代表的《真美善》作家群;以夏莱蒂、林微音、朱维基为代表的“绿社”,以及新感觉派作家如叶灵凤、施蛰存、穆时英等人。总体而言,大部分海派文人都加入了这场关于肉体的书写过程。
第二节 “花一般的罪恶”:一朵移栽的“恶之花”
一、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
法国作家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在唯美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位置。在他之前,美国的爱伦·坡已经进行了“纯诗”的探索,波德莱尔把爱伦·坡的《神秘及幻想故事集》(Tales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译成法语,他的《埃德加·坡的小说》以及其他散文也体现出坡的诗学思想的影响,波德莱尔自身的观念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英国仰慕者斯温伯恩。
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出版于 1857 年,这部诗集将现代社会的病态之美纤毫毕现地展现出来。中国作家邵洵美于 1928 年,也就是距离《恶之花》诞生 70 年之际,出版了他带有模仿意味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同一年,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开始了他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后来,尽管这个研究计划还未全部完成本雅明便去世了,但他的研究成果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小册子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成为分析波德莱尔作品的重要参考。
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而言,波德莱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周作人、田汉、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均有对他的译介文字,诗人李金发、艾青、闻一多也有受了他的启发而创作的诗作,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也不过是其中之一。李欧梵认为,《花一般的罪恶》这个书名,“来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另外也可能参照了乔治·摩尔的《激情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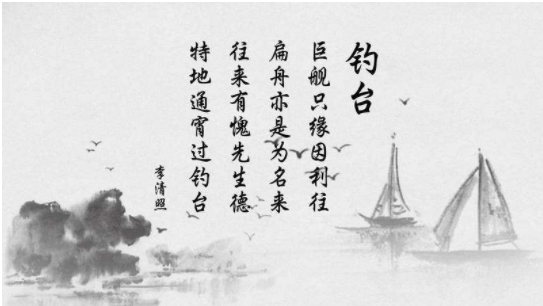
结语
费孝通曾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但是在文学艺术的内部,常常是“美美”无法“与共”。不必说传统之美与现代之美的差异,也不必说本民族之美与异族之美的不同,单是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同一思潮流派。所谓的“京派”唯美与“海派”唯美就显示出鲜明的差别。
唯美主义运动的发生即是形式美对古典美的一种反击,恶之美对善之美的发难,偏邪之美对中正之美的摧残;而占据了大部分历史时期的“真善美”,也并非甘拜下风,它处于社会的主流地位,对这种叛逆式的唯美主张采取了家长式的规训与惩戒。1857 年 6 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刚刚出版便遭查禁,他给萨巴蒂埃夫人写信求助希望她出庭作证,证明《恶之花》中有 9 首诗歌是写给她的情诗,可是她没有出庭。1895 年,站在法庭上的王尔德着装时髦而精致,唯“美”是从的追求使他无可挽回地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艺术家的身份终究未能战胜世俗偏见。然而,美终究战胜了时间,唯美的作品最终得到了认可。
可是,处在不同空间中的人们对异质美的接受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法国人接受《恶之花》可能只需要数月,英国人接受《道连·格雷的画像》可能需要数年,当人们接受了这种异质美的时候,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了。当中国文学开始接受唯美主义思想时,唯美主义已经是一个被定格在欧洲的、世纪末的历史词汇了。“当郁达夫先生介绍《黄面志》时,事实上这个刊物在英国停刊已久,有关诸人士都已经去世,‘世纪末’早已成为过去,新世纪也开始了四分之一。”163中国作家接受的,又如何是当时饱受争议的唯美主义呢?拉开了历史与国度的距离,也并不意味着“美”与“美”之间就能和平“与共”。周作人曾说:“平心的说,这种叙述(指“猥亵”的内容)在学术上自有适当的地位”,可是他在指责那些描绘官能的海派作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时,却没能守住他的“平心”;鲁迅一面斥责叶灵凤对比亚兹莱的仿作是“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的拙作,一面却大赞比亚兹莱的画“多么纯净与美丽”,也在卧室里挂起裸体画。究竟是“美”的不能“与共”,还是人的不能“与共”呢?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