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密切,二者相互影响,渗透,以及因此产生变革。其中小说的影视化改编己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这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愈演愈烈。
第一章 严歌苓小说的大众化倾向
第一节 奇观化的叙事策略
“奇观”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他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2]在 1975 年,美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将“奇观”一词引入电影研究范畴,她在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写道:“作为起点,本文提出电影是怎样反思、揭示,甚至利用社会所承认的对性的差异可作的直截了当的阐释,也就是那种控制着形象、色情的看的方式以及奇观的阐释。”[1]她认为,电影中的奇观性与性别差异及其呈现的方式密切相关。穆尔维运用精神分析和女性视角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女性作为男性观众欲望的对象,在一种不平等关系中被置于被动的、被人观看和被展示的位置上,而男性则是主动的、“看”的载体;二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自恋要求和观看癖,女性身体便不自觉地成为了被看对象。电影或者其他媒介会选择以视觉快感为轴心来安排,从而影片的叙事性有所减弱。实际上,“奇观化”理论不仅应用于影视业,已经扩大到整个文化市场。无论是演出业、图书报刊业、音像业、娱乐业、还是艺术品经营业、网络文化业,要么借“奇观化”作为适应时代潮流的一种绚烂夺目的外在包装,要么借“奇观化”作为迎合消费市场的营销手段,不管是哪一种,它背后所暗藏和隐喻的则是人们审美旨趣的转变和精神层面的日渐空虚。在文学领域,“奇观化”的书写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有意为之,是极致的、猎奇的,同时也是感官的,欲望化的。这种奇观化书写不仅是取材的奇巧还有体现在对叙事策略的处理上,一方面为了迎合受众的幻想性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符合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而最终直指的则是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性。
.............................
第二章 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特质
第一节 强烈的画面感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画面是电影语言基本的元素,它是电影的原材料。”[2]严歌苓小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极强的画面感。她在创作过程中有意突破传统的叙事方式,融入了具有影像化特征以及影视美学思维的手法和技巧,使其小说的视觉化叙事具有含蓄简约的特征,通过更为直观、立体、生动的方式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人生众态“浮世绘”,同时不断激发读者的视觉和情感的想象力,从而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色彩
在艺术世界中,色彩是我们视觉审美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色彩也一直是视觉艺术的创作和审美中心。同样,色彩融入到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也为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撼。作品中通过将不同色彩组合、转换的方式,不仅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可感性,再加上色彩与特定意象的组合,而且更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譬如,在小说《红罗裙》中,海云中意了许久的一条夕阳红的太阳裙,正是她对美好青春的追求以及生命活力的展现,也是对女性欲望的间接表达;《雌性的草地》中的红色代表沈红霞,“红马”则象征着革命理想。沈红霞以其自身为榜样,成为牧马班里的思想标杆,却也渐渐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在追逐“理想”的道理上一去不复返。小说结尾,当“我”重返草原偶遇了独自牧马的沈红霞,她几乎全身赤裸,斜挎着一只红布包。她早已丢弃了象征肉体负累的衣物,仅剩的“皮带”和“鲜红的小布包”代表的则是永不褪色的革命理想。在《扶桑》中,红色作为代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传统颜色在这部小说中反复被呈现出来,开篇便写道:“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1]除此之外,与“红色”相关的意象组合多达几十处,扶桑身着“红绸衫”,漆成粉红色的墙,竹床上悬着的粉红帐子,两只尖足上的粉红袜子和红鞋,桌上点着的红蜡烛……这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为扶桑这名东方名妓定下了古老神秘而又美丽迷人的东方基调。当许多年后,七十岁的克里斯回忆起扶桑,是她身着浅红色衫子跪着的形象。克里斯在风烛残年的年纪才领悟到,自己的一生是被一个妓女宽恕下来的,而那浅红色的衫子正如扶桑一样,单薄、残破,却包藏了无尽的污浊和不堪。因而,小说中的“红色”被陈思和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扶桑所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如同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扶桑若作一个具体的妓女来理解,那是缩小其艺术内涵,她是一种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2]这种力量和文化正是通过扶桑身上的红衫得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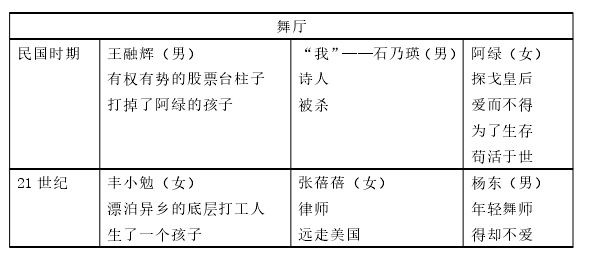
严歌苓小说影视元素问题研究
.............................
第三章 严歌苓小说影视元素的启示
第一节 文学与影视相互促进
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艺术形式,影视艺术在一路吸收包纳其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并一步步发展壮大。在艺术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由于其兼具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美学特质,便与影视自然产生密切的联系。世界上第一部改编电影《月球旅行记》(1902)就是乔治·梅里爱改编自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 H.G.威尔斯的小说《最早登上月球的人》。在我国,第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是于1921 年上映,由法国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姐妹》改编而来的《红粉骷髅》,也由此迈出了文学与影视联姻的第一步。接着是 1924 年由郑正秋担任编剧,由徐琥、张石川执导,改编自徐枕亚同名小说《玉梨魂》的上映,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也让早期的电影创作者们看到了文学与影视联姻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期。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思潮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由此形成了各种文学风格、流派。这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也是电影改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电影改编对原作的选择主要是现代文学作品和创作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鲁迅诞辰 100 周年之际,他的三部小说(《伤逝》《阿Q 正传》和《药》)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开启了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经典电影改编的新篇章。此后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相继被改编成电影。改编现代文学经典的原因一是小说中有现成的布景、情节和人物。改编已有的故事和剧本,要比重新创作一个脚本更加容易。二是借文学的威望来提高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三是改编不用担心意识形态上的非议。创作于七八十年代的小说也成为电影改编的另一选择。选择同时期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一是这些原著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所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都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二是改编这类文学作品相对于改编文学经典压力较小,在视听语言的表达上相对自由。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电影改编在内容思想和主题风格上都保持着与原著的一致性,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改编,显示出对原著较高的贴合性,文学居于主导地位,显示出电影对文学的高度依赖性。
............................
第二节 文学与影视合谋的隐患
文学与影视联姻的确为文学拓宽了传播渠道,并衍生了新的文学样式。但文学与影视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文学作为一种能够带领读者探索精神世界的精英文化,与影视的大众文化诉求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因此,在当下市场语境中,文学与影视合谋后,在影视媒介的强势影响下,文学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从本体意义上压缩了文学的生存空间;同时在影视化改编带来的丰厚商业利润面前,许多作家放弃了对纯文学的坚守,转而投身影视编剧行列。文学与影视的合谋,也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埋下了商业隐患。
首先,影视改编消解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使文学由雅变俗走向商业化。由于影视在创作生产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投资成本的问题,于是制片方会想尽一切办法吸引观众的眼球,就会导致影视过于追求故事元素,而忽略了文学元素。结果就是,许多小说被改编后,只能看到相似的故事,却稀释甚至消散了原著的人文底蕴。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小姨多鹤》改编的电视剧大体上保留了原著的故事脉络,但一经比较,发现改编后的二次创作与原作的精神内涵相去甚远。原著中朱小环之于多鹤,一开始是嫉妒,因为她自己丧失了生育能力,将自己心爱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分享,是她所不能接受的,直到张俭和多鹤去小环娘家将她接回来这才不情愿地接受了。另一次与多鹤产生隔阂的时候是她知道张俭和多鹤在外面偷情,小环对多鹤和张俭建立多年的信任轰然坍塌了,她感受到来自两个家人的背叛,但是小环选择了包容,默默消化委屈和伤心。当一家人经历了无数磨难后,多鹤对于小环,对于这个家,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张俭进监狱后,是小环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甚至在多鹤产生自杀念头的时候,是小环的坚强和乐观触动了她,打消了轻生的想法。小说中的小环是一个善良、乐观、坚强的女性。而经过电视剧改编的朱小环,俨然成了一个打翻醋坛子的泼妇,身上的人性光辉荡然无存,人物也变得扁平化;甚至还把原著中小环坚强、善良的美好品质移植到多鹤身上。更甚的是,电视剧《小姨多鹤》二次上映时,直接将多鹤日本人的身份改成了中国人,原著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已消失殆尽。

严歌苓小说影视元素问题研究
...............................
结语 新媒体时代,文学何为
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小说与影视之间的亲密互动已成为一种潮流,作家纷纷“触电”,参与影视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借助影视媒介的传播,为原著带来了更多的目光,为作家也带来了名利双收的鲜花与掌声。但同时,作家也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困境:在创作中如何处理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坚持写作的特性和品格,自觉维护文学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歌苓成为我们研究新媒体时代如何处理文学与传媒关系的最有价值的个案。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已成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特征,“生产和消费——它们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的。”[1]因此,消费社会背景下,媒介已成为文学生产、消费的重要环节介入到文学产业中。新传媒时代,媒介无论作为消解还是建构的力量,对文学而言都是一次新的革命。一方面媒介将文学从政治权力话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打破了垄断,重构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多元格局。但同时,媒介又对文学形成了新的威胁,即商业化的加重。因此,在看到传媒为文学提供生成空间和消费场域,拓展传播渠道时,同时也要看到它对文学自由与个性的限制也越来越鲜明。在新传媒时代文学是回归了自身,还是背离了自身,越走越远,最后都只能由文学自身来做出回答。
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密切,二者相互影响,渗透,以及因此产生变革。其中小说的影视化改编己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这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愈演愈烈。因此,利用、依托大众传媒,是文学在传媒时代的必然,对此,文学一方面要做的是对新的传播方式理智接受,主动适应大众传媒时代,并将其作为新契机,在冲突与融合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学不能迷失自我,沦陷为大众传媒的附庸和傀儡。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的心灵家园,仍然要坚守文学的价值标准,坚守人文主义的信念与理想,拥有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自身的独立特性和品质,在此基础上求得新媒体时代文学新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严歌苓为我们提供了新媒体时代文学与传媒关系的典型样本。可以看到,严歌苓一直努力地在文学与影视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她积极迎合市场的需求,在创作中注重大众文化的倾向,以利于更好地通过与传媒的合作拓展受众群体与传播渠道,求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这种取向会带来潜在的危机,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本质,丧失文学的自由。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