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论文,具体“名号”因“人声”而得,“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说文解字·音》),故董仲舒言“诗道志”;喉舌之音同其它万物的对应,自然较之“音乐”对生发时空的分域之感受更为直接质朴,它是声响同事物的直接呼应,故董仲舒言其“长于质”。在宗周承上代的祭祀活动中,不仅“乐语”的教授系统得以衍生,“乐语”同“音乐”相合参与祭祀的体系同样被编辑和完善。与最工整的“颂”乐相应,产生了同“天文”相合的“颂”体诗,为祭祀“书典”的成型提供了直接语料;与最活跃的“风”乐相应,产生了同“人文”相应的“风”诗,为“乐语”系统提供了持久的活源;二者的交融,使“形四方风”(《毛诗序》)的“《诗》《书》、执礼,皆雅言”(《论语·述而》)系统生出,且在长期祭祀中成为拥有权威立场的情志表述体统。随着宗族力量的衰落,执礼行人作为“诗礼”的直接参与者,对上述过程进行了脱离祭祀场域的再造。在这一过程中,“诗”在“阕”的基础上开始了整篇、断句乃至单独语词的被用。其中既有对既成章句在原生环境下的借用,也更多呈现出“断章赋诗”“唯我所取”的变用。伴随着这一进程,“诗”在祭祀中作为“乐语”的神圣性开始消失,而逐渐成为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固定意义表述。在截断的章句中,这些意义可以按照实践需要,被取用于各类场景中;在对语词的单独讲述中,宗周以““乐语”教国子”的言词意义开始在行人之间被再定义,并在原有形态下阐述新的文化适宜。
........
绪论
欲达成对董学阐释体系更加深入的探近,必须对其前身作历史性考察,并对其同时期的经学阐释作协同关注。然而由于不同时期历史真实的留存具有不同“当下”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空缺性,因此对董子之学所生出的不同时期的阐释偏见进行关注也是理解董子阐释的必要补充。从董子生世致力铸构的经学将成,到晚清诸贤极力挽扶的经学就木;从不同现代理论对董子阐释的自由批判,到现代阐释学视域下董子阐释的再发掘……经学体系这一“若循环”的共业为中华文明的传递和繁盛所付出的担当,总使董子阐释在文化的转折时期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董子作为经学体系初具形态的关键留影,更是泽及整个经学时代的阐释格局初型。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意到了前人较少关注的“乐咏德,故长于风”在董仲舒理论体系中的深刻内涵,从董仲舒关注到的“气同则会,声比则应”角度发掘了“乐”为董仲舒阐释体系奠基的可能性。其次,深入分析了《乐》《诗》《春秋》在承担人文意义阐释架构中分别具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在董仲舒“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阐释特征形成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它们在董仲舒的阐释体系中各自分担了何种阐释功能。同时,本文还注意到了宗周对《诗》的生成,荆楚王国对《诗》与《春秋》的替位,以及楚汉帝国的统治者对《春秋》正式进入义理言说领域所起的作用。与前人大多单独讨论董仲舒同《公羊》学的关联有所不同,本文从董仲舒、陆贾、贾谊共同参与楚汉王朝文化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比较了《春秋》三传在汉初的文化建构意义及其对董仲舒用《春秋》的影响
.......
第一章辅乐与和乐:宗周用《诗》的本能①与可能
第一节音声之域与和乐之宜
祭祀过程中产生的歌谣,同样是“圣人”“体其义而节文之”的结果,是对人在特定情境下用气发声的体察和定位。一方面,在“五声”之文的基础上,“八器之音”相杂成“文”的功用使得“音乐”较长期地保持了意义阐释体系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管弦乐(尤其管乐)通天文的长期实践,早期中国这一地区的语音受“八风之音”相变成“文”的影响,为后世语音出现独特的音调表意奠定了基础。音调的和音色在祭祀乐理实践中的需求,使得“节奏”的极为丰富成为必须。在器乐之音的对应下,喉舌之音作为天然造型最丰富的孔窍,产生了相应的言语音位。成为“有节于外”的言语之“音”。“祭”时之“志”的传达所依赖“歌谣”,是不同音位的言语之声相应相杂的结果。歌谣的“阙”显然是在祭祀之“乐”的演奏中形成的特征。在“音乐”为群体察祭活动的主要组织和架构活动的时代,“诗乐舞”一体为用,语音一开始作为辅助性元素存在,同样仅有小部分群体参与使用。在先民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声响”作为“接序”事、物的重要载体,为人文实践构建起了万物互通的场域。更清晰地描述出《公羊》学派在武帝朝率先出位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明白地解释了董仲舒《春秋》之学同三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阐释义理的角度揭橥了董仲舒构建“三统三世”的立体结构对《公羊》学在汉代为《春秋》立于王官所起的作用。此外,还说明了这一时期《诗》和《春秋》同样作为经学阐释重镇在文化建构中的各自偏重。
第二节人声的出位与人情的探进
在“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的构架之下,各类自然之物都有了进入较集中时空的可能,成为紧凑的虚拟“天时”“地理”系统。这些“幽隐”不可见的情状在祭祀中以“音乐”为载体,进入了不同时空内天文、人文可体察的范围。在人为的编辑过程中,“物相杂”(《周易·系辞下》)有了更加明白的“斯文”(《论语·子罕》)特征。“四时不同气,气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不同事物在这一体系中被载录,最初缘于其在不同天时、地理中的生发时机,即事物本身的“迟速”(《左传·昭公元年》)统天地阴阳的“缓急”(《如天之为第八十》)在适当时空的契合。这是人类编辑自然声响而成“斯文”的最早实践体系之一,也是随后各类体系得以生成的基础。在对稳固“天文”的参照之下,人文阐释产生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的权威性可能。“音乐”由此具有了描述事物存在“适宜”的“咏德”之功效,人类实践也由此进入了“凡事预则立”(《礼记·中庸》)的历史,人类文明则由此进入到可被追忆的时代。随着这一体系的不断完善,宗周一代出现了文、武两朝替乐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在“器乐之音”基础上,“言语之音”开始出现,并逐渐在祭祀实践中成熟。得益于更为丰富的音位和更加便捷的形式,“语音”对意义场域的建构更加准确,运用也更加自由,逐渐接替了器乐之音而开启了更广阔的人文意义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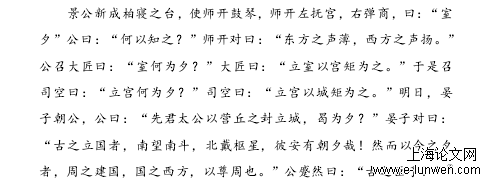
第三章诗赋与辞赋:楚地用《诗》的摹象与习玩..............................................83
第一节诗境的移用与共用..................................................................................83
第二节骚体的借位与还释..................................................................................90
小结..........................................................................................................................98
第四章失位与变位:董子阐《诗》的脱乐和史化..............................................100
第一节乐的缺位与一统的缓冲........................................................................100
第二节《诗》的补位与新乐的酝酿................................................................109
小结........................................................................................................................119
第五章替生与共生:“乐语”与“文辞”的交接..............................................121
第一节祀典的生成与“春秋”的实践............................................................121
第二节“五行”替“乐”与《春秋》接《诗》............................................131
小结........................................................................................................................141
第一节诗境的移用与共用..................................................................................83
第二节骚体的借位与还释..................................................................................90
小结..........................................................................................................................98
第四章失位与变位:董子阐《诗》的脱乐和史化..............................................100
第一节乐的缺位与一统的缓冲........................................................................100
第二节《诗》的补位与新乐的酝酿................................................................109
小结........................................................................................................................119
第五章替生与共生:“乐语”与“文辞”的交接..............................................121
第一节祀典的生成与“春秋”的实践............................................................121
第二节“五行”替“乐”与《春秋》接《诗》............................................131
小结........................................................................................................................141
.......
第六章《春秋》学的义理与“无达辞”的节文
第一节《穀梁》《左氏》的立场与《春秋》为用
值得注意的是,陆贾和贾谊二人作为汉初大儒,都看到了《春秋》作为公共义理言说的场域所本,在引用前学时都以《春秋》作为构建人文意义体系的义理根基;并就《穀梁》学和《左氏》学之长,依照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作出了同当朝人文建构需求相应的意义阐释体系建构;但二者都没有囿于其中一家,而是分别就两家《春秋》之长取以为干,并对别家治《春秋》法进行并取。蔡忠道先生见《新语》“除了引《穀梁》外,也有征引《公羊》《左传》,不过,份量不及《穀梁》多。因此,评定陆贾为汉初的《穀梁》大师时,应注意的是,陆贾的经学是秦代的经学,并无汉儒门户之见,因此兼通三传,而最重《穀梁》”①;同时,贾谊在引用《春秋》时也没有避开对左氏之外诸家的运用。在《新书·礼》阐述“一国馀粮之蓄”时,详细论述了“饥年之礼”的问题。《穀梁》襄公二十四年同样有对经文“大饥”的详细解释以及应对措施的详细设定②,较之《公羊·庄公二十八年》传“臧孙辰告籴于齐”时简单解释“告籴”何以为“讥”③,可知贾谊对《穀梁》之义亦有取用。
第二节董仲舒用《公羊》及其对《春秋》阐释场域的建构
如依文献学家言,则以上举例皆是后学蹿入而导致的不同《春秋》学派之间义理交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公羊》学派取其说理义之便而成其论的结果。之所以不同于陆贾、贾谊对《穀梁》《左氏》学理内涵的运用,是由于董仲舒正值武帝构建王朝意义阐释体系时期,《公羊》之学历史性地承担起对《春秋》这一意义阐释场域的“节文”,开启了以《春秋》论意义适宜的经学时代。在孝武着力构建汉家王朝人文阐释系统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以《公羊》之学接替《穀梁》和《左氏》的学理所长,在对《春秋》之事的具体阐释中,为“《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楚庄王第一》)的“无达辞”(《精华第五》)提供了合理的分域。董仲舒不仅以《公羊》“大一统”为基理,借三家学对“鬼”“神”“人”的义理侧重分生出了“三统”,更借助“礼”的意义阐释过程,对“三世”“异辞”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情”“理”分域。这样,《公羊》学的义理之长最终得以完满体现——以一家之学汇通三家之长,使《春秋》在理论上成为一个立体、流动且可循环的完备意义阐释场域。在此基础上,受训诂之学的时代风尚影响,董仲舒对构成《春秋》的文辞进行了突破说理场域的分析,从言辞本身的名号意义出发,将《公羊》以《春秋》当新王的义理阐释系统同现世人类情性进行了接通,使《春秋》在葆有论义说理完整性的同时,具有了现世义理教化活源的开放性特征。同时,董仲舒提出了“得”的概念,使得《春秋》这一新时期人文阐释系统的文辞优长被大幅度开发出来。对“适宜”的探索就此在文辞的承载之下成为“得”与“不得”之间的永恒过程,正所谓“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正贯第十一》)。
.......
结语
在中介天文运转和人文实践的阐释过程中,“音乐”有了同天文“节气”一样的丰富“节文”特征,产生了“阕”的范畴。同时以其与“气”一样“盈于四海”的特质,在中介“斯文”的同时,为单独的声响提供了与万物接通之域中的位置。在“器乐之音”的丰富实践中,人窍的“言语之音”随着“音乐”系统形成了便捷丰富的音位“乐语”系统。从《舜典》中帝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到宗周以““乐语”教国子”(《周礼·春官》),“乐”不仅以“德音”的身份在早期察祭活动中联结了人同自然,更为人的“言语之音”形成系统提供了框架。无论“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正贯第十一》)对“情亦性也”(《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的理论发明,抑或“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玉杯第二》)论人之间意义的接通应用,其实都是“乐咏德,故长于风”的早期人文实践积累所得。《诗》作为“斯文”阐释的担当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脱离了祭祀环境,为随后诸子在失乐的历史时期对《诗》进行义理再造提供了实践先导,也为汉初《诗》以“训诂”为端在学派间兴起指明了可能之方向。总之,董仲舒的经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在顺应了汉武帝文化建构需求的同时,因其所处的人文精神转生背景,往往成为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人文阐释无法绕过的源头。首先,“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阐释理念,使得“五经”作为周秦文化共业,在阐释《十九章》的过程中得以留存和复生。其次,在“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董仲舒传》)的同时,董仲舒对阐释载体历史性替位的敏锐把握,使得《春秋》之学借《公羊》派之长登上人文阐释的前台,成为后世经、史共同关注的学术重镇。不仅太史公受其影响,其文化创造同样“着眼于《春秋》的现实政治功效”①,即便“晚清将公羊学推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代表人物”②康有为,亦以董学为标榜,著《春秋董氏学》以发己意,宣其应新世、用新法的文化阐释意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