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阎连科的“第三种乡土写作”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憾,但是它仍然代表了当代乡土写作的一种走向、补充,也说明了作家对于乡土写作的深入思考。在阎连科持续三十余年的创作当中,始终呈现着一个关于时代、内心与写作的芜杂梦境。在传统现实主义和作家心中自觉的写作约束面前,阎连科试图从生命个体的内在真实出发,用内心的冲突来厘清现实。
一.“神实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创作
(一)心灵:现实之“神”
何为现实?这实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几乎每一位作家都会在写作过程中思考他们诉诸笔端的背景和故事从何而来、如何呈现,有何所指。对于作家而言,在他们所处的、看到的、想象的现实背后,往往涉及了更为深广的维度。而不同维度下的现实观,主导着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品,产生了迥异的审美、社会意味。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广泛地涉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将作家的不同现实观归纳为“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灵魂真实”,为自己的写作铺垫了详实的理论支撑,也为我们开拓了认知现实的新视角。
我们注意到,阎连科所提到的四种现实观念,就前两种现实观而言,与中国近现代史、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走向有着一定的契合。我认为,在“控构真实”范畴当中存在两种角度,一种是完全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但是,这种情形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渐渐退隐。然而,随着文化审查制度的存在、作家写作的规约,另一种潜在的“控构”渐渐浮出水面,即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地规避、疏远权力和政治。事实上,这正是政治与制度“取胜”的结果。在阎连科看来,“真正的开明、进步与开放,是要允许作家对日常、细碎和人的情感、情调、情绪及由此牵涉的人之内心、灵魂的关心与关注;但同时也要允许并鼓励作家由于社会的现实,对人的生存处境的逼迫、挤压所造成的境遇的思考与关注。”①因为这种“控构”的存在,与之相伴相生的必然是对它的抵挡。于是,也就有了世相真实的存在。如三四十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作家以及当代文学中的“新写实”作家,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对都市生活的细致描摹、浮游于时代之上的生命体验的认同感而收获成功的。但是,这种现实观主导下的写作在为世俗真实不惜文墨、乐此不疲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对生命真实进一步逼近的可能。从以上思考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阎连科所主张的现实观,实际上包含着对“控构”和“世相”的反叛,也是对以往传统现实观的突围。那么,又如何突围呢?
...........................
(二)现实中展开的审美之途
中国独特的发展走向,使它有着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社会现实,因而在文学创作中,就需要寻找到契合自身的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来身体力行地支撑中国本土写作。就呈现现实而言,描摹看上去是一个“安全”的策略。在当下,一些作家也特别注重在叙事中去复刻现实、使用既有的写作经验。但是,这种写作观念常常会使文字更加干枯、生硬。同时,他们的创作习惯和当下现实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生活选择发生着重叠。在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和现实生态等多重因素裹挟的复杂环境中,人们思维的僵化和虚弱亟待转变。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作家开始了对这一写作惯性的突破。他们在作品当中将荒诞、颓败、想象浸入到现实当中,使得现实似乎不再那么真实,但却让读者感受到与当下时代的种种契合,以及未曾有过的审美感受。阎连科试图突破既定的文学范式和流行的文学模式,思考呈现现实的方式,突围出新的可能。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对“神实主义”作如下阐释: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实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①也就是说,阎连科主张用审美的、文学的眼光去看待现实。正如孙郁所说:“神实主义的最大可能是在颠倒的逻辑里展开审美之途,那些概念是以感性的心灵律动写就的。”②说到底,文学的功用在于审美,文学区别于哲学、报道等实用类文章的关键也在于它的丰富内蕴和审美性。这不仅解释了阎连科作品中对现实看似离谱的书写方式,也表明了阎连科试图对以往错误文学理念、文学功用的否定。在阎连科看来,作家应当以一种文学的方式介入到现实中去,在现实中展开审美之途。朱光潜曾将我们日常面对的的现实生活称作“物甲”,把以作家为主体,所看到的掌握的现实生活比作“物乙”。显然,“物乙”是源自“物甲”的,但两者又存在不同。“物甲”不具有主观性,“物乙”却由于为作家思索之物,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性,甚至可能包括作家的想象。童庆炳根据朱光潜先生对现实的划分方式,对现实和作家笔下的现实作以甄别,从而对文学的审美范式进行梳理: “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如实描写生活本身,而是指作家所虚构、所想象、所描写的对象的内在逻辑性。”③这样,或许基本上阐释出为何在文学作品当中,有些事物在读者眼中看似离奇,但揣摩起来,却愈发觉得与现实有着某种契合。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或许能够有所启发,即不应该太过纠结与事物与现实本身是否一致,而是看它的内里是否有着某种深意与现实达成了共识,这种表达本身又产生了怎样的审美意味。或者说,当我们注意到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某些“离谱”之处时,就更加需要注意的是作家为何要这样表达,因为这是否源自现实带给作家的启示或不满,正是这一点,就与阎连科的文学理念不谋而合。
..........................
二.破解灵魂之“役”
(一)从“耙耧虚境”走出
贾平凹说:“云层上面都是阳光,至于如何穿破云层,各民族有各民族自己的云梯。”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界开始尝试与世界文学接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思潮渐次涌入。与此同时,先锋作家们试图硬性植入西方的文学理念和形式,但由于中西方不同的现实处境,只能渐渐归于平静。寻根文学也曾试图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找到一种契合,虽然留给我们许多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但突破仍有所空缺。总的来讲,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寻根文学,作家、理论家始终在寻求一条融合了西方的文学观念与中国自身写作传统、现实的本土化写作之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本土的民间资源,他们以较为平和的心态展开叙述,按照中国的文化积淀、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生活状貌来呈现现代性与现实主义,彰显出中国文学写作的独特性。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就是这方面探索的杰出代表,而在众多作家当中,阎连科更是本土化写作中较为特殊的一位。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将“神实主义”的理念加入到本土化当中。纵观阎连科近十余年的长篇小说,从《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到《四书》、《炸裂志》、《日熄》,文本中的地理背景都坐落于一片名为“耙耧”的群山之中。这片虚构的山脉,几乎具备了乡土中国的全部可能。阎连科将想象与我国中原地区湿热而黏重的土壤相结合。于是,“耙耧山脉”成为了阎连科“神实主义”创作与乡土写作结合的独特场域。
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闭塞、萧索、绝静,给人以“荒寒”之感,这也是阎连科小说美学形态的现实依据和渊薮。人们世代以农耕为生,在靠天吃饭的岁月里,人们不但要承受天灾,还随时处于“人祸”的风险当中。“人祸”则既包括时代更迭带来的阵痛,也包含着由于农民文化性格、国民性等因素泛起的涟漪。阎连科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地方色彩,可以说是灰暗色调中夹杂着血汁的。我们从他的描摹当中可以看到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的错综结合。此外,在风土人情方面,“耙耧山脉”杂糅着中国本土化的宗教观念、民间文化信仰,轮回转世观念、鬼魂观念、风水信仰、文化心理、思维特征、集体无意识等等。人们说话的方式、活动表演语言也与河南的豫剧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试图将烙着地域文化印记的主观情愫融入到乡土小说叙事空间之中。#p#分页标题#e#
..............................
(二)冷硬的“血色与荒寒”
时代、环境、生存现状常常与作家的写作动机、母题、风格彼此交融,相互关联,形成某种独特的“气味”。我们发现,作家在现实和人性中往返时,作品中时常散发着一股“血气”。血腥,通常象征着杀戮、暴力、狂热、牺牲。它也暗示着一种动荡不安、波澜起伏的状态。莫言《酒国》中的侏儒“杀婴炒菜”、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靠“处女膜”发财,还有《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靠着卖血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作家们通过对流血、肉体的残忍想象,极致、夸张地书写了在物质的强烈刺激之下,异化、病态、崩溃的人性。在这些作家当中,阎连科是将这种“血肉化残酷书写”作惯性呈现的一位。纵观阎连科的“耙耧”系列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贯穿着身体书写、疾病隐喻。这种书写渗透在乡土写作中,让我们思考,血腥的背后还原了什么,这份残酷当中蕴藉着哪些意味。
从文本当中,我们发现,阎连科通过发现残缺、疾病的身体,来揭示乡土中的苦难和逼仄。在阎连科所营造出来的乡土之中,饥饿、贫困、疾病、死亡这些苦难往往与“靠天吃饭的农民”如影相伴。通过疾病的隐喻,阎连科写出了农民们糟糕的生存环境,将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化作一种动态的、意绪化的痛苦生动地呈现出来。可以说,阎连科笔下的乡土世界是溃败的。无论是人们的基本生存、生活,还是在现代社会下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皆无法得到保证。在《日光流年》中,生活在“耙耧”深山中三姓村的村民们始终都在被“喉堵症”带来的无法预知的死亡危险摧残着。《受活》当中,在深山的褶皱里的受活人无一不是盲、瘸、聋、儒。他们的生死在自然灾害和贫穷的裹挟中薄如蝉翼。②此外,“耙耧”深处的居民,不仅缺失先天的健康,生来就受到死亡的威胁,在面对天灾时,也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化的“自杀式”反抗,纵然这种反抗往往是失败的。《日光流年》中,面对饥荒,男人们去卖腿皮、女人出去卖肉体,来换得粮食;由于司马笑笑的错误指挥导致庄稼颗粒无收之后,为了让更多的人活命,大家将有残缺的孩子放在深山当中,乌鸦吃掉他们的身体和尸体之后,人们再去吃这些乌鸦;司马笑笑为了自罚,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拿自己的身体去喂乌鸦;《坚硬如水》中,夏红梅由于饥饿,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被野蛮地占有,最终撑死在墓穴当中……阎连科这样关于生命存在的绝望情境层出不穷。在前者的基础上,辅之以冷峻有力、又宏观壮阔的强烈又残酷描写,使得文本蕴含了强烈的“荒寒”美感。这种“荒寒”美感首先就表现在人们基本生存本能面前的无能为力上。我们常常说,“食色性也”。套用现在对这句话的表述,“食”、“色”是人们恒久不变的生存本能。阎连科通过极端的手法,把底层农民的基本生活欲求难于满足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将艰涩的生存困境完全铺陈在读者眼前,疮痍满目、惨不忍睹。
.................................
三 、涨溢的文体“新质”...........................17
(一)声音:多声部叙事与作家介入...........................17
(二)神话的节奏变体...................19
(三)挣脱日光下的魔影......................21
三.涨溢的文体“新质”
(一)声音:多声部叙事与作家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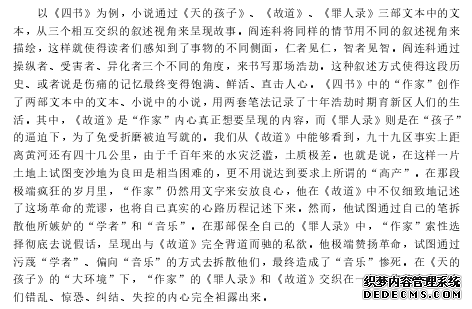
........................
结论
(一)“第三种乡土写作”概念界定
循着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轨迹,我们从阎连科的“神实主义”理念出发,结合阎连科的“耙耧”系列长篇小说,爬梳作品中所涵盖的社会、政治、文化内蕴,探索作品的文体形式。从这些梳理中,虽然不能对阎连科提出的“第三种乡土写作”作以下定义式的判断,但是可以大致归纳出“第三种乡土写作”的一些基本面貌、方向和价值.
首先,“第三种乡土写作”在面对中国现当代乡土写作发展时,是继承与剥离同在的。关键的衔接点在于不重于描摹现实,而是重于探求现实。阎连科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传统时说过,想在这两种传统中走出与众不同的第三条道路来。通过对他的创作理念、文本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所谈到的“第三条道路”并不囿于对以往传统的完全背离,而是一种“扬弃”。这其中,既存在批判国民性,汲取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也带有着对中国的现实始终没有绝望,仍旧坚执地朝前走的气魄。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始终是具备着中国乡土的真实性的同时,也勾画了当下、未来乡土中国意绪化的可能性。“耙耧”山脉这一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写作发生地,正是阎连科进行乡土写作、探索乡土、中国社会现实的场域。阎连科从乡土出发,却以一种看似“不忠于”乡土的方式来书写乡土:既不是纯理性地烛照、批判,也不完全沉浸在理想、古典之中,而是通过基于“神实”的风水、风俗、风情,为乡土小说找到了新的赖以生存的依托。
其次,“第三种乡土写作”文本呈现出的乡土,是经由内心过滤之后的乡土,并注重在现实中展开了文学的审美之途。阎连科将独有的情感作为现实存在的艺术高度与标码,以心灵去关照时代,以真实的情感去抒写时代。阎连科始终认为,作品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探索、突围现实。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会无病呻吟,因而,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是自信的,即使面对繁复的文化语境他可能会不被理解,他也毅然选择依靠自己的心灵去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丁帆曾说:“任何一个民族和阶级的作家都希望站在自己的视域内,用乡土小说这个‘载体’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①阎连科将现实、人性,历史、时代艺术地整合到一起,将自己的理解用与之最相贴切的文体形式写出来。可以说,他的心灵就是“第三种乡土写作”的核心枢纽。阎连科独一无二的写作风格源自独一无二的情感,在现实土壤上,神话、寓言、梦境等等,都是 “神实主义”通向真实、现实的渠道。同时,阎连科在描摹现实时,也关注到了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以上两者成为他“神实主义”的重要支撑,也是他乡土写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略)
试论阎连科的“第三种乡土写作”--以“耙耧”系列长篇文学小说为例
- 论文价格:免费
- 用途: ---
- 作者:上海论文网
- 点击次数:77
- 论文字数:0
- 论文编号:el2019090710401719276
- 日期:2019-07-20
- 来源:上海论文网
T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