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毕飞宇小说形式层面的心理蕴涵
1.1 毕飞宇小说语言的心理蕴涵
毕飞宇小说的语言属于文学语言,要分析毕飞宇小说语言的心理蕴涵,首先要对文学语言的心理蕴涵进行界定。本文沿用童庆炳对其的定义:“文学语言的心理蕴涵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组织所表述或暗示的人的心理体验状态。”②文学作品的语言组织总是能包孕着丰富的心理蕴涵,并能在读者中唤起特定的心理反应,这使得对文学语言加以心理学分析成为必要。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语言中的一切,包括它的物质的和机械的表现,比如声音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心理的。”③本文谨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毕飞宇小说语言的心理蕴涵:陌生化、音乐性、本色化、辞格的运用。
1.1.1 陌生化及其心理蕴涵
陌生化理论最先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①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要设法延长。这个观点讲述了形式展现与读者感受的关系,其实已经初步显示出形式的陌生化与心理学的关系。
童庆炳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再次阐述,他认为,语言的陌生化并不只是为着新奇,而是通过新奇使人从对生活的漠然或麻木状态下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恢复对生活的感觉。概述之,就是为着使读者产生新鲜的体验。
毕飞宇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主要通过“公众话语的个人化解释”和成语的移用来实现。
第三章 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及其心理蕴涵 ............................ 25
首先是“公众话语的个人化解释”。这是由赵允芳提出的一个观点,她认为毕飞宇小说语风里时常有意识形态性的词汇,也许可以这样说,毕飞宇小说语言里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对意识形态性公众话语的移用,并在这种移用的过程中构成一种突出的语风,作者把这种高频率存在于小说里的语风归结为公众话语的个人化解释。毕飞宇的这种“公众话语的个人化解释”恰好形成了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如在《玉米》中,王家庄的支书王连方被撤职之后决定学一门手艺,他选择这门手艺的过程是极其“科学”的,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他时常一手执烟,一手叉腰,站到《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面前,把箍桶匠、杀猪匠、鞋匠、篾匠、铁匠、铜匠、锡匠、木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里而外、由现象到本质,再联系上自己的身体、年纪、精力、威望等实际,决定做漆匠。”②毕飞宇把哲学里认识论的方法论用到了王连方做决定的过程中,一是符合王连方的身份,作为村支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必然是了解的,但也正因为他只是一个村支书,所以他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尚停留在大而空的层面。此刻他用这个理论来论证自己未来的职业,有一种大材小用的滑稽感,这种滑稽感是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的。二是营造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哲学语言的插入消解了文学语言的优美、感性,形成了一种中和的、硬朗的、个性化的语言风格。《玉秧》中亦有体现,在文章结尾,被抓到的八二(3)班班主任彭老师于凌晨 5 点逃跑,钱主任却说:“他没有逃掉,他怎么能逃得掉呢?他掉进了人民的汪洋大海。”
..........................
1.2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心理蕴涵
小说的叙述行为、情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作家特定的心理动机和心理过程,这心理动机和心理过程隐藏在作家和读者习以为常的叙事结构之中,唯有深究才得以呈现。毕飞宇后期的作品并不刻意学习和模仿某种小说结构,而是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去确定结构,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有仅适用于它自己的独特的结构。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结构我们可以推测出作者在构思和书写这部作品时的独特的心理动机和心理过程。
1.2.1 叙述行为及其心理蕴涵
关于何为叙述行为,童庆炳如是写道:“艺术家的叙述行为就是如何运用言词来创造一个幻想世界的举动。”①弗洛伊德认为,言词的宣泄和叙述行为的分界线在于叙事技巧,是叙事技巧使得一般性的言词表达成为人们可以接受并争相效仿的艺术行动。因此,叙述行为较之单纯的言词宣泄对于读者有着更大的、更长久的魅力。对由叙述行为所规范的世界的向往和模仿是大多数作家的共同心理体验,他们由模仿而衍生出的新的创造亦为后人提供了模仿的对象。
..........................
1.2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心理蕴涵
小说的叙述行为、情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作家特定的心理动机和心理过程,这心理动机和心理过程隐藏在作家和读者习以为常的叙事结构之中,唯有深究才得以呈现。毕飞宇后期的作品并不刻意学习和模仿某种小说结构,而是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去确定结构,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有仅适用于它自己的独特的结构。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结构我们可以推测出作者在构思和书写这部作品时的独特的心理动机和心理过程。
1.2.1 叙述行为及其心理蕴涵
关于何为叙述行为,童庆炳如是写道:“艺术家的叙述行为就是如何运用言词来创造一个幻想世界的举动。”①弗洛伊德认为,言词的宣泄和叙述行为的分界线在于叙事技巧,是叙事技巧使得一般性的言词表达成为人们可以接受并争相效仿的艺术行动。因此,叙述行为较之单纯的言词宣泄对于读者有着更大的、更长久的魅力。对由叙述行为所规范的世界的向往和模仿是大多数作家的共同心理体验,他们由模仿而衍生出的新的创造亦为后人提供了模仿的对象。
毕飞宇有作为普通人言词宣泄的需要,也有作为作家的自觉和克制,所以他的作品不单是为了满足他言词宣泄的心理欲望,更多的是对由叙述行为所规范的世界的模仿和创新。他的短篇小说《蛐蛐 蛐蛐》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蒲松龄《促织》的模仿和创新,是对《促织》的致敬。《蛐蛐 蛐蛐》与《促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它们的命名,无关历史、悲欢、愤世嫉俗和悲天悯人,只是以这种小虫的名字命名,颇有一种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观感;如它们的隐喻性,蒲松龄借古讽今,用明朝宣德年间因“宫中尚促织之戏”而引发的悲喜来讽刺他所在的清朝的种种不端,而文中所述促织,自成名儿子落井之后已是其儿子所变,故其后所写促织的神态表现其实也就是描写其小儿的神思情态,写促织也就是写人,甚至是写人不如促织,促织使成名免去了刑罚,获得了荣华富贵,人却不能。毕飞宇则更为直接,开头即说天下所有的蛐蛐都是死人所变,故之后所写蛐蛐,必定离不开它生前所对应的人的事迹。作者创造了二呆这个人物,由他来联系阴阳两界,能联系得了阴阳两界的人必定能捉到战无不胜的蛐蛐,因为他是盯着活着的人去揣测蛐蛐的战斗力的。敲钟的小老头的坟墓被二呆盯上了,小老头一个人来到了村里,又一个人默默地去世,孤寂的亡灵有可能成为最凶狠的蛐蛐,因为有着无尽的委屈和怨念,这怨念里尽是人间的冷漠、驱逐和疏离;如它们的真实性,人变促织和死人变蛐蛐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小说具有了传奇性,但这传奇性是建立在日常真实的基础上的,蒲松龄仅安排小孩变的促织斗得过鸡,而不是牛羊和老虎等大型兽类,是其真实性的体现。并且,唯有鸡会主动攻击促织,争斗才有开始的契机。毕飞宇文中并不是把所有的死人都变成了蛐蛐,幺妹就没有,它是跌入长江淹死的,不具有变成地面上的蛐蛐的可能性,于是作者让她变成了鱼,这才具有可信度和真实性。当然,此处所说的真实是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真实和科学真实。另外,《蛐蛐 蛐蛐》与《促织》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或者说是基于时代而产生的创新。首先,基于时代的不同,它们所谏讽的内容不同,《促织》借以明朝为背景的故事来劝谏大清皇帝勤政爱民,谨言慎行。《蛐蛐 蛐蛐》则是通过蛐蛐之间的残忍争斗和全面自卫来揭示特殊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防备。其次,毕飞宇除却描述了蛐蛐、人和时代的关系外,还另加入了对底层群体的描述。底层群体的愚昧、漠然和集群特征加速了下乡知识分子悲剧的发生。
...........................
第二章 毕飞宇小说内容层面的心理蕴涵
2.1 毕飞宇小说人物的心理蕴涵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心理内涵,但文学评论界往往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诚然,一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与其所揭示的社会内容密切相关,但首要的却是因为它以审美形态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在与人物的心理共鸣中产生对位效应。另外,人物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人物的心理内涵其实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文学的特征规范着我们,只有掌握了个别才能真正掌握一般。因此,本文在分析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把重点放在分析其小说人物的心理内涵上,在文艺心理学视域下,心理内涵也即心理蕴涵。
2.1.1 人物的心理矛盾
...........................
第二章 毕飞宇小说内容层面的心理蕴涵
2.1 毕飞宇小说人物的心理蕴涵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心理内涵,但文学评论界往往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诚然,一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与其所揭示的社会内容密切相关,但首要的却是因为它以审美形态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在与人物的心理共鸣中产生对位效应。另外,人物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人物的心理内涵其实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文学的特征规范着我们,只有掌握了个别才能真正掌握一般。因此,本文在分析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把重点放在分析其小说人物的心理内涵上,在文艺心理学视域下,心理内涵也即心理蕴涵。
2.1.1 人物的心理矛盾
人本主义心理学把人的基本需求从低至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更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但这样的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会有变化,也会有种种例外。人的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会带来人的心理矛盾,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内心冲突的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丰富的、奇特的心理世界。#p#分页标题#e#
毕飞宇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亦经历着种种心理矛盾的折磨,如在《青衣》中,筱燕秋早年在对登台的愿望和对老一辈青衣的尊重之间徘徊不定,受尽折磨。她最终无法抵御舞台的诱惑,次次登台,没有给嫦娥的 B 档演员李雪芬出演的机会。唯一一次李雪芬基于观众基础在部队演出结束之后,筱燕秋冷眼相对,极尽嘲讽,并在冲动之下朝李雪芬泼了热水,自毁前程。这自然是一个戏痴因对角色的沉迷而对常规和道德的忽视和对抗,也是心理冲突解决的一个方案:一方对另一方的战胜。后来,《奔月》获投资得以重新排演,筱燕秋在挽留春来和自己出演之间犹豫,最终为了把春来留下而主动出让 A 档嫦娥的角色。到正式演出时,筱燕秋戏痴的本色占了上风,她不让,一连演了四场,直到最后自己身体有恙赶不上演出,依然披了戏衣在雪地里演给虚空,演给自己。《奔月》复演的整个过程其实是筱燕秋无比纠结和矛盾的过程,她自然有“我就是嫦娥”的坚持和自信,但亦有身体发福的忧虑和李雪芬事件的创伤。但最终,这忧虑和创伤都未能改变她戏痴的本色,一旦上台,她还是二十年前的筱燕秋。说到底,筱燕秋的心理矛盾不过是意识和潜意识的争斗,意识为人制定了许多规则:尊老,爱幼。筱燕秋是无意违抗这些规则的,她不想得罪李雪芬,也想挽留住春来,但在她的潜意识里,对嫦娥这一角色太痴迷了,痴迷到影响了意识,打破了规则。
..............................
2.2 毕飞宇小说母题的心理蕴涵
母题在文学理论中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作品中表现主题或情节的最小单位,二是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因素。但文艺心理学视域下对其的解释可能有所不同,这里沿用曾军、邓金明为其所下的定义:“母题就是在跨越时代和语种的无数作品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作品中被不断重复的无意识欲望。”①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毕飞宇小说作品中不断重复的无意识愿望都是对“疼痛”和“恐惧”的展示和宣泄,因此“疼痛”和“恐惧”就成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个母题。母题可以通过意象表现出来,意象又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我们一一论述。
2.2.1 毕飞宇小说中的“疼痛”母题
无论是所谓的城市书写还是乡村描述,毕飞宇的小说中无不弥漫着深深的疼痛之感。究其原因,一是童年所经历的“文革”对其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人生中的反复辗转所产生的漂泊感,三是对血缘和种姓的追寻所产生的惶惑和猜疑。这些情绪郁结在毕飞宇内心深处,他在他的散文中坦白陈述,在小说中则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发泄出来,也正是借助文字,虽不可解心结,但可缓解一二。
《玉秀》的故事发生在“文革”结束的第六年,此时的大学校园里,告密和猜忌之风仍旧盛行。玉秧被揭发,之后又揭发别人,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甚至为此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校卫队。师与生,师与师,生与生之间的关系彻底沦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畸形,信任和温情变得遥不可及。玉秧本是一个单纯朴实的乡村姑娘,靠着笨拙的死记硬背把自己送进了城里,她是王家庄的骄傲,却在城里受尽折辱,终于也对环境妥协,成了那污浊的一部分。玉秧是带着一路心伤走到最后的,同学的排挤、班主任的轻视、学校的怀疑、恋爱的失意,她小小年纪,却似乎已历经沧桑,只是这沧桑却掩不去她眼中童稚的迷茫。她是感受得到疼痛的,只是这疼痛是很私人的、很自我的,超脱不掉时代,甚至超脱不掉她所在的那个校园。作者是在后来的时光写给后来的人看的,因此作者和读者的疼痛更多的是对于那个年代,对于那种畸形的人际的伤感和反省。《上海往事》中,小金宝和臭蛋都是离开家乡到大上海漂泊,到最后却都违了初心,再也无法回归平静祥和的生活。小金宝企图挽救臭蛋和阿娇,不让他们步自己的后尘,却未能成功。臭蛋已深陷其中,抽身不得,也不愿抽身,阿娇呢,则因着对上海天真的向往而飞蛾扑火。上海因着它灯红酒绿的魅惑而延续着这一代代的轮回,剧中人因自己的遭际和结局而悲痛,读者则因这无法打破的轮回而悲痛。《叙事》中,主人公是一个史学硕士,致力于自己家族史的追寻,追寻至奶奶婉怡这里却遇到了阻碍,这是一个陆家竭力遗忘的、从不提起的过往。父亲很可能是奶奶婉仪和日本人板本六郎的孩子,这个发现对主人公的影响很深,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产生厌倦,
2.2 毕飞宇小说母题的心理蕴涵
母题在文学理论中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作品中表现主题或情节的最小单位,二是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因素。但文艺心理学视域下对其的解释可能有所不同,这里沿用曾军、邓金明为其所下的定义:“母题就是在跨越时代和语种的无数作品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作品中被不断重复的无意识欲望。”①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毕飞宇小说作品中不断重复的无意识愿望都是对“疼痛”和“恐惧”的展示和宣泄,因此“疼痛”和“恐惧”就成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个母题。母题可以通过意象表现出来,意象又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我们一一论述。
2.2.1 毕飞宇小说中的“疼痛”母题
无论是所谓的城市书写还是乡村描述,毕飞宇的小说中无不弥漫着深深的疼痛之感。究其原因,一是童年所经历的“文革”对其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人生中的反复辗转所产生的漂泊感,三是对血缘和种姓的追寻所产生的惶惑和猜疑。这些情绪郁结在毕飞宇内心深处,他在他的散文中坦白陈述,在小说中则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发泄出来,也正是借助文字,虽不可解心结,但可缓解一二。
《玉秀》的故事发生在“文革”结束的第六年,此时的大学校园里,告密和猜忌之风仍旧盛行。玉秧被揭发,之后又揭发别人,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甚至为此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校卫队。师与生,师与师,生与生之间的关系彻底沦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畸形,信任和温情变得遥不可及。玉秧本是一个单纯朴实的乡村姑娘,靠着笨拙的死记硬背把自己送进了城里,她是王家庄的骄傲,却在城里受尽折辱,终于也对环境妥协,成了那污浊的一部分。玉秧是带着一路心伤走到最后的,同学的排挤、班主任的轻视、学校的怀疑、恋爱的失意,她小小年纪,却似乎已历经沧桑,只是这沧桑却掩不去她眼中童稚的迷茫。她是感受得到疼痛的,只是这疼痛是很私人的、很自我的,超脱不掉时代,甚至超脱不掉她所在的那个校园。作者是在后来的时光写给后来的人看的,因此作者和读者的疼痛更多的是对于那个年代,对于那种畸形的人际的伤感和反省。《上海往事》中,小金宝和臭蛋都是离开家乡到大上海漂泊,到最后却都违了初心,再也无法回归平静祥和的生活。小金宝企图挽救臭蛋和阿娇,不让他们步自己的后尘,却未能成功。臭蛋已深陷其中,抽身不得,也不愿抽身,阿娇呢,则因着对上海天真的向往而飞蛾扑火。上海因着它灯红酒绿的魅惑而延续着这一代代的轮回,剧中人因自己的遭际和结局而悲痛,读者则因这无法打破的轮回而悲痛。《叙事》中,主人公是一个史学硕士,致力于自己家族史的追寻,追寻至奶奶婉怡这里却遇到了阻碍,这是一个陆家竭力遗忘的、从不提起的过往。父亲很可能是奶奶婉仪和日本人板本六郎的孩子,这个发现对主人公的影响很深,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产生厌倦,
离家出走,四处飘泊。以上三种有关“疼痛”的心理体验皆是来自作者现实中的心理历程,移时换景,在虚构的故事里展现出来。它不是毕飞宇某一部作品的主题,而是其许多作品共同的母题。
............................
............................
3.1 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 ....................................... 25
3.2 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的心理蕴涵 ............................... 27
第三章 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及其心理蕴涵
3.1 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
3.1.1 题材吁求形式
作家在获得题材之后,转而寻找形式来表现题材,这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后题材变为内容,获得审美效果,获得读者,失败后题材停留在题材的阶段,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形式是否能出现,以何种方式出现,取决于题材是否有吁求,题材对形式有何种限制和要求,从这个层面来说,题材征服形式。
毕飞宇在其散文《谁也不能哭出来》中自述了其小说《雨天的棉花糖》的创作过程。首先是题材的获得,毕飞宇没有参军的经历,所以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而是从旁人的记录和口述中获得。这个旁人,是毕飞宇一个学生的二姐夫,一个看似很弱势的人,一个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并安全归来的人。题材有了,那以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结构记录下这个故事呢?作者看到了《新闻联播》的几个画面,老布什迎接美国战俘,战俘与亲人幸福拥抱。这些画面与作者听到的“二姐夫”的故事大相径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对比使作者决定写一个中国战俘的故事,小说的主题便定了下来。这应是一个悲剧,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故事。因此,小说的语言必然是绵长的、哀伤的,是欲说还休的,是隐秘的。在人称的选择上,作者也大费周章,在小说即将写完时选择把人称由第三人称换为第一人称,以此来贴近人物和表现主题。这里的题材是“二姐夫”的参战经历和战后变化,通过语言和人称等形式的加工,变成《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的人生经历,也即作品的内容。这是一个成功的题材吁求形式的实例,由于题材的出现,作者开始寻求恰当的形式来表达内容,尽管题材对形式有种种要求,但作者一一满足,这就成就了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毕飞宇在其散文《<推拿>的一点题外话》中提到了其小说《推拿》的题材获得和意欲表达的主题,题材源自作者六十年代的乡村经验,在物质基础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娱乐的对象转向了身边人,通常是残疾人,因为不同,因为无害。
............................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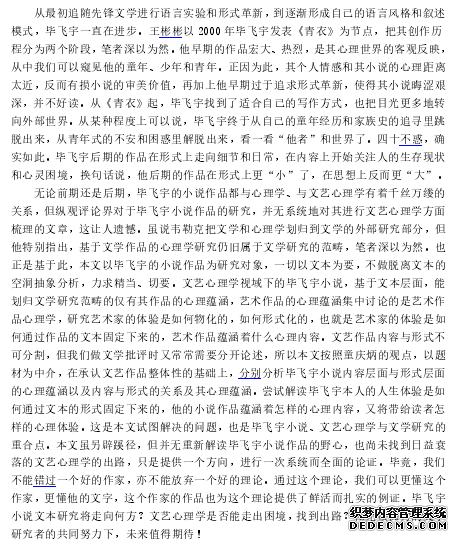
参考文献(略)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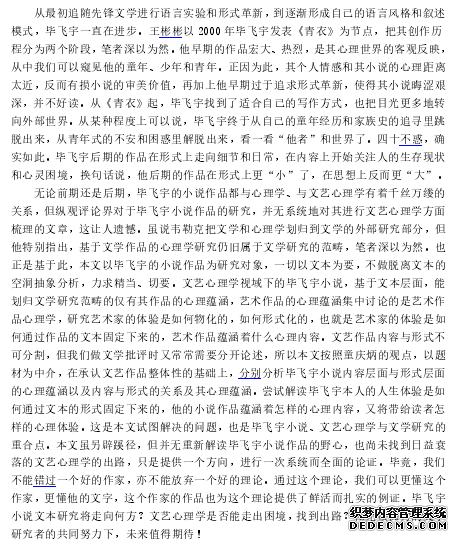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