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任氏兄弟儿童文学乡土叙事内容
第一节乡土苦难中的人性之美
尽管任氏兄弟对故乡和童年怀有深厚的爱心,但是他们也不能无视浙东水乡人民的苦难去编缀童梦。乡土的苦难,一开始就成为了他们乡土叙事创作中的共同主题。在任氏兄弟的作品中苦难非常普遍:战争、饥饿、失学、瘟疫、压迫等,每一项都能使人挫败,但任氏兄弟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向我们表达这种负面的情绪,而是想在这种苦难的背景下,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笔触,讴歌乡土人民的淳朴、善良的心地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挖掘苦难中凸显的人性之美。在作品中这种苦难中的人性之美表现在多方面:浓浓亲情、真挚友情、邻里互助情,这种充满爱意的情感使得作品总是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健康状态,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善意是可以克服天灾人祸,成为大家渡过难关的精神支柱。
一、乡土苦难中的浓浓亲情
亲情是我们无法选择也割舍不掉的,自古以来就是被歌颂的对象,在战乱困苦的年代,乡土成为了苦难和温情并存的世界,愈是艰苦的处境愈能凸显亲情可贵与感人。任氏兄弟笔下的乡土苦难中的浓浓亲情是全方位的,有袓孙之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这些浓厚的亲情背后,更多的是展现长辈对于孩子的无限爱意,凸显出人物的人性之光。这种默默无私的爱总是让人灵魂一怔,是感动亦是感情。任大霖《掇夜人的孩子》中,“我”从小跟着外婆生活,家境极其寒酸,“我”在学校的生活更是惨不忍睹,外婆为了让我补充营养,夜晚偷偷地去当“掇夜人”赚得那两个画了鬼脸的鸡蛋。夜里凉了,外婆把唯一的棉袄盖在我的身上,自己却经受夜的寒凉。而“我”不能接受外婆是“掇夜人”的身份,一方面是因为不忍心让外婆去做这么低贱的职业,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想在同学面前被嘲笑,自己的外婆居然是“掇夜人”,自己每天加餐的鸡蛋居然是鬼蛋!外婆就在不断的操劳中悲惨地死去了,而外婆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仔细地刷洗那两个她前一天当“掇夜人”赚来的鬼蛋,直到洁白的蛋壳上连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外婆的爱孙之心到最后“我”才领悟,自己的私心是多么的可悲,这种矛盾的张力更加凸显了外婆对“我”深深的爱意。任大星《三个铜板豆腐》中祖孙之情同样震撼人心,“我”和弟弟初次去到外婆家,“我们”第一次尝到了世界上豆腐这样的美味,看到弟弟在饭桌下把在老母鸡嘴喙边上的豆腐抢了过来,“外婆本来好端端的一脸笑容,但这时候突然用手心往脸上一抹,竟抹下了两大滴眼泪,扑扑掉到饭桌上。”
..............................
第二节新旧时代乡土少年儿童的心灵变迁
在写作内容上,任氏兄弟乡土叙事既写新时代的乡土儿童生活,又写旧时代的乡土儿童生活,一个真正洞察儿童心灵的作家,是应该也必须能够写出不同历史时期儿童心灵的鲜明时代特征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旧时代的乡土儿童是被奴役了的少年,他们心底总是笼罩着一层阴影,背负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和精神负担,缺乏自立的能力,略显早熟的‘小大人’,总是处在沉思与忧郁之中,而新时代的乡土儿童,他们是时代的主人,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小主人公们再也不是含恨凝愁、压抑忧伤的模样,在阳光下,他们的精神解放了,枷锁砸碎了,焕发出心中全部的美的意蕴。”氏兄弟准确地把握住了新旧时代乡土儿童心灵的变迁,写出了不同时代乡土儿童的心理特征。
一、旧时代奴役的阴影
鲁迅小说中塑造的祥林嫂、闰土是其乡土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他们是旧社会被奴役的对象。祥林嫂是集勤劳、善良、质朴为一身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在旧社会她却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她的一生都活在灰色调中,她是被封建社会奴役的妇女。少年闰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中年闰土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这种性格转变也具有“传承性”,闰土的孩子水生也继承了这样的命运:懂事后的呆滞麻木。而在任氏兄弟的笔下,这种被奴役的对象年纪更小,常言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就懂事的孩子也早早蒙上了灰色的调调,儿童总是呈现出压抑、忧伤的面与姿态。特别是在任大霖的作品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任大霖《风筝》中,贵松哥花三天辛辛苦苦地做自己喜欢的风筝,为了赚钱养家他一言不发就抛弃他辛苦做的风筝,忘记与玩伴的游戏,只身去杭州做生意,等他再回到家时:“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两年前的贵松哥哥了。他白胖,文静;他穿着黑布长衫,戴着一顶瓜皮帽,帽上还装着个红顶。只是这顶瓜皮帽,就可以充分说明他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大人了,虽然他的身材告诉我们:他只有十三岁。”懂事的贵松哥不能再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只知道从早忙到晚,整天板着脸,把“笑”忘记了,更不要说“玩”了,他既不会爬到樟树上去捣鸟蛋,也不会放风筝,真正的贵松哥去哪里了呢?贵松哥的突然“成熟”,是病态社会对少年儿童狀害的结果。“
............................
第二章任氏兄弟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特色
第一节童年经验下的儿童叙事视角
“在诸多的叙事策略中,儿童叙事视角的采用,最能体现作家对童年经验的深刻体验。肇始于1911年鲁迅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全知成人视角模式,引入儿童视角,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多样化的先声。’”此后,很多作家都纷纷开始采用童年视角进行叙事,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不少色彩。“儿童视角使作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和立场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借助于这一视角,作家主体还原到逼真的儿童心态和视界,重新体验了对世界的认识,在陌生化的体验中重构了一个区别于成人理性的艺术世界。实际上,发生在作家与儿童经验、儿童视角之间的这种亲和性和吸引力首先来自于儿童本体所蕴含的巨大魅力。”任氏兄弟在浙东乡村度过了他们大部分的青少年时光,当他们离开故乡踏入城市后,这份已在心底烙下深刻印记的乡土童年经验却早己在心里燃起热情的火焰,渴望追溯童年的生活,任氏兄弟便不约而同地纷纷采用了儿童叙事视角进行乡土叙事。“童年经验下的儿童视角的采用意味着叙事由现在时返回过去从而获得隐含的历史纵深感,童年尖锐敏感的直觉体验让作者可借童年记忆的叙事直陈人类的生存境遇,并对成人日趋规整僵硬的话语世界产生解构效应。”可见,童年经验下的儿童叙事视角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功能:一是直陈人类的生存境遇,二是解构成人世界。任氏兄弟儿童文学乡土叙事作品中大部分都是采用了儿童叙事视角,其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恰好承担了以上前两种重要职能:用儿童纯净的视角来打量社会,直述乡土人家的生存境遇,揭示乡土的苦难事实;儿童未经理性侵染的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思维,表现出对成人世界的解构。
.........................
第二节第一人称乡土叙事的巧妙继承
对于中国的乡土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策略几乎是一种传统。“第一人称视角策略在故乡小说中的运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一方面代表着叙事主体对表述内容的评价愿望,另一方面在见证故乡生活和表达现代意识方面可以有不同的效果。鲁迅的故乡小说几乎全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而且身份几乎都是回乡客。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在鲁迅这里更多地是因为‘我’更能表述‘自我’在‘故乡’面前的位置和感受。新时期以后的故乡小说中,对于故乡的表述大多数作家再次采取了鲁迅的第一人称视角’策略,其原因在于,第一人称视角在故乡叙事中似乎更能渗透叙事主体对于故乡的情绪。”
在任氏兄弟的乡土儿童文学作品中,广泛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巧妙沿袭了鲁迅第一人称乡土叙事的风格,一方面通过叙事者职能的灵活变换、反观式的忆态结构和童年体验再现的方式,将第一人称“我”之外的乡土视野尽可能还原给读者,增强整体文本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第一人称叙事的优势,对儿童的语言、行为、心理进行全面的描绘,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对主人公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描绘,表现出叙述主体对故乡的评价,渗透出叙述主体对于故乡的情绪。#p#分页标题#e#
.........................
第三章任氏兄弟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的价值和意义...........45
第一节奠定了中国当代儿童小说最初的“乡土性’’............45
第二节呈现出新时期儿童文学最初的“悲剧............45
第三节感动今世的情感力量............45
第三章任氏兄弟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节奠定了中国当代儿竃小说最初的“乡土性”
丁帆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梳理了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概念阈定与演变,他准确地把握到了乡土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认同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概念阈定、政治化过程中乡土小说概念阈定的蜕变与断裂、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概念阈定的复归与新变。”任大霖最具代表性的儿童乡土文学作品诞生在丁帆所梳理的第二个阶段,即政治化过程中乡土小说概念阈定的蜕变和断裂阶段,在这个蜕变和断裂的时期,政治因素的强力渗透,乡土文学可想而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丁帆所说:“可以明显地看出,建国以后的乡土小说逐渐放弃了对‘地方特色’和‘风俗画面’的描写,就剩下题材和内容贴近于‘乡土’而已。……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概念就与‘农村题材小说’等同,殊不知乡土小说的三大要义(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才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三十年中,中国乡土小说除剩下题材特征外,其概念的阈限已是没有疆域了,乃至在^大一统’的三突出’原则下,根本消灭了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形成了乡土小说历史沿革的断裂带。”他在论述五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困惑时也高度简要地总结出了这时期的乡土小说的真实形态:“民间话语文化精神的抽空;价值参照系的失落及政治化;美学形态的附属性;风俗风景地域风情的符号化……结果必然是乡土文学的政治空洞化与形式化:与五十年代大陆其他文学式样一样,乡土小说成了政治的传声筒。”陈国和也在其《当代性与新世纪乡村小说研宄》中谈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乡村小说对乡村的想象方式是革命性的,小说中的乡村图景也是革命性的,小说内涵也就失去了乡土小说固有的审美风格。
.......................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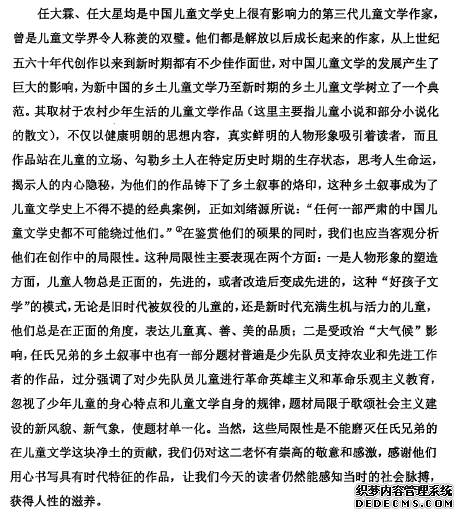
参考文献(略)

